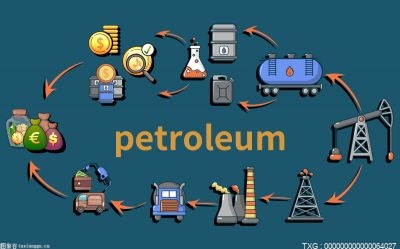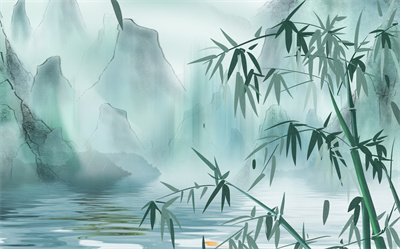“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作为最基层的公务员,乡镇干部始终处在第一线,各项决策部署最终要依靠基层党员干部穿针引线、落到实处。
乡镇公务员的日常是什么样的?他们经历着怎样的人间烟火?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茅奖作家陈彦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重点观照基层公务员群体,叙写他们日常的琐碎与坚守。
历时八年、九易其稿。陈彦这部51万字长篇小说,讲述位于秦岭大山深处的北斗镇北斗村,一棵长在两家地畔子中间的百年老树被偷,旋即引发数个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拥有半棵树产权的温如风面对“村霸”孙铁锤的欺骗、侮辱,毅然走上利益诉求的上访之路;小镇公务员安北斗则一次次奔波在劝访路上。后来雪球越滚越大,各色人物、多个家庭、众多事件牵连其中。安北斗从无奈、气愤,到理解、同情,再到最后主动为温如风寻求正义,中国基层社会生态在细水微澜的描写中全景式呈现。
 【资料图】
【资料图】
“这些看似零零碎碎、甚至鸡毛蒜皮的事情,却牵动着老百姓的‘面子’‘里子’,甚至精神深层的痛快与痛恨。解决好这些利益诉求与纠纷是挺大的事。我希望贴近生活去写,写出我所体悟到的那种质感。”陈彦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乡镇公务员直接面对的是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最终都要靠最基层的干部去干、去办、去处理。因此工作日常要有温度,要耐得住纷繁琐碎。”
陈彦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他一直坚持为普通人立传,著有戏曲代表作“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以及长篇小说《装台》《主角》《喜剧》等,其中《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陈彦(受访者供图)
谈创作主题“基层工作零零碎碎、甚至鸡毛蒜皮,牵动着老百姓的‘面子’‘里子’,我希望写出那种质感”
新京报: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关注上访的并不多。为何会关注这一主题?可以谈谈创作初衷吗?
陈彦:严格讲,上访只是小说整体故事的一个起因,一个生长点。由这个生长点出发,可以拉开乡村生活的复杂面向,很多人物也因这条线索的存在逐渐被牵扯其中。因此,这个生长点虽然不是全书的重心,但也有它的意义。勤劳的村民温如风突然丢了半棵树,一棵树长在两家地畔子中间,他只有半棵的所有权。为这半棵树,他本来也不值得如此去淘神费力。可偷了树的人不仅不认账,而且还找着茬地欺侮他,这就引发了长时间关于“半棵树”的利益诉求问题。
我对乡村生活有较深印象,小时候随同在乡镇做公务员的父亲,迁徙过五个乡镇,至今也还有在乡镇做公务员的亲戚,知道基层工作的零零碎碎、甚至鸡毛蒜皮。正是这些看似不重要的事情,却牵动着老百姓的“面子”“里子”,甚至精神深层的痛快与痛恨。解决好这些利益诉求与纠纷,其实是挺大的事。我希望贴近生活去写,写出我所体悟到的那种质感。当然,也希望能够写得开阔一些,打开的生活面向更丰富一些。
新京报:这一题材创作难度在哪里?
陈彦:难度在解决好这半棵树的利益诉求与乡村整体建设发展的彼此照应上。不能只看到“半棵树”,要看到乡村发展的整体进程,要有大的眼光和格局。小说发生时间离我们并不遥远,开头的时候,一些人腰里还别着BB机。整体乡村还都在发展、甚至在反复试错阶段。各种利益诉求,带来了矛盾的复杂化、尖锐性。但政府始终在努力改变现状。比如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也是在得到沉痛教训后的渐次开悟升华。
我希望写出这个过程,写出挫折中反复突围挺进的艰难姿态,以及逐渐打开的美好愿景。
新京报:这部小说历时八年、九易其稿,既重点观照小镇公务员群体,也写了各种各样的村民、市民,全景式呈现中国基层社会生态。从人物极简入场,到最后呈现出一个庞大的复杂社会结构,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全新的写作探索?
陈彦:对于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来讲,每一次创作其实都是一次探索。长篇小说由于体量的原因,网状结构居多,其结构自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但在阅读越来越成为碎片化的时代,长篇小说写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每一个写作者,总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当然不是迎合,但需要做相互适恰的调试。像十九世纪西方长篇小说那样一开始就拉开成千上万字的景物、各色人等的静态描写的方式,明显不适应今天的阅读节奏。尤其是一开头就拉开十分复杂的面向,有可能让读者一头雾水。我是希望从最简单的地方进入,顺着纲线,进入网状的事件,也包括网状的人际与人性的复杂结构,最终完成一部心中的多声部的生命交响。
新京报:小说围绕星空与半棵树两条脉络,为何选择这样的写作视角?如何理解“星空与半棵树”这个意象?
陈彦:星空是自然的、高蹈的、精神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有超越性的,而半棵树则代表着人间烟火,一地琐碎。我执意要在这部小说中写这么多有关星空的东西,首先也是来自少年时期对乡村那个美丽星空的记忆。
那时没有光污染这一说,在乡村晚上能看到最美妙的夜空。真是“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它们就在头顶游动、闪烁。有时觉得天空就像一顶很深的帽子,深深扣在山梁、河流、大树上。就连看流星雨也是常有的事。这种天文现象的刻骨铭心,让我始终有一种想细致书写的冲动,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方式。
因为此前创作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基本生活场域都在城市。城市能看到的星星比乡村少了。尽管如此,我在《主角》中,仍有不少篇幅在对这种夜空进行详细描写。而这部书就有了较多的切入关系,让星空与这片土地和人物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进行更多的自然与精神的观照。至于半棵树与星空的关系,既是表征的,也是内里的,意义希望是多重的,但它的简单向度仍是精神与物质、辽阔与狭小、诗性与现实的对照。
谈人物塑造“乡镇公务员实在不易,大大小小的事,最终都要靠最基层的干部去干、去办、去处理”
新京报:小说主人公安北斗,代表了小镇公务员的百味日常——他们需要承受各种压力,坚守初心,做好每一件小事,实现自我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你了解到的小镇公务员真实状态是怎么样的?
陈彦:他们实在不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大大小小的事,最终都要靠最基层的干部去干、去办、去处理,也可以叫兜底。他们直接面对的是群众,很多话都需朝实里说,朝心上走,说大话没有用,具体问题抹也抹不过去,搪塞更是搪塞不住的,就得想方设法去解决。
我印象中,父亲做乡长、书记时,经常在乡下走动着。有时即使在机关,一旦说哪里有事,转身就走。有些地方能骑自行车,有些地方还得靠两腿走。他下乡时经常手里握着一根竹棍,一是防狗,二是防路边草丛中的蛇。乡间经常发生的事,就是失火、走蛟(山体滑坡)、打死架(有时带着家族性、群体性)。当然,也有为鸡蛋的所有权、地畔子、房界桩等事体,闹得不可开交的。有些处理不了,就坐到家里不走,吃饭时端起碗就吃,晚上还要卧下。感觉工作特别难做。这里面有胡搅蛮缠的,但多数还是要靠工作方法和家长里短的情感去加以解决。
小说里所涉及的基层干部,比如安北斗、比如牛栏山、比如南归雁等,他们还是有做基层干部的情怀的,至于有的脱离实际,想为穷山僻壤发展经济,结果弄出一些乌龙、荒诞来,那恰恰是“星空与半棵树”之间的错位与生命局限。而像孙铁锤这样的“村霸”,那又是另一种人性恶的“奇葩盛开”。文学在这两个维度上,自然就有了书写的张力。
新京报:安北斗充满了人性的复杂、人心的煎熬、人际的纷繁。正面人物如何塑造才能不简单化、概念化?难度大吗?
陈彦:我觉得塑造正面人物是最难的创作,无论戏剧、影视、小说皆然。因为“反面人物”,甚至“恶之花”,容易集大成,形成鲜明的性格特点,包括语言特色。其实绝对的“反面人物”大概是没有的。坏到“头上长疮,脚下流脓”,他也可能有爱的人,愿意为之付出一些牺牲,闪现一点人性的火光。总之,丰富性是容易体现的。
而“正面人物”大家要求就会很多,他身上出现一点瑕疵,连受众也要讨伐作者在“胡写”。但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越是对主人公寄托了更高的审美理想,就越是需要写出这个人物的丰富性、甚至复杂性来,开掘的深度越深,这个人物就越发可信。靠说大话、靠贴标签,甚至一味去拔高、提纯,只会让创作初衷越来越虚浮、各色。
小说的一号人物是安北斗,他在上大学时,爱上了天文观测,最后考上公务员,分到一个小镇上,业余爱好始终还在。且这个小镇又是一个特别适合天文观测的地方,完全可以满足他仰望星空的精神需求。但他又不得不面对属于他的工作日常,那就是“半棵树”、甚至还有比半棵树更小的事体。一切都在消磨,都在耗损,包括爱情、家庭、事业,他需要适应、需要坚守。坚守的过程中充满了无语、无助、无奈,时有放弃的念头和很深的挫败感,但也逐渐清晰了一个精神生命的无愧底色。
新京报:书中另一个主角温如风,作为半棵树产权的主人,本在查找无果后放弃了寻找,可不时受到周围人的讥讽嘲笑,偶然得知真相后,踏上了寻找尊严与公平的道路,搭上了10年光阴。温如风是不是太执着了?
陈彦:温如风的本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民。他本来已过上小康生活,也已越过可以不在意那“半棵树”的物质上的纠缠,但“村霸”孙铁锤对他的欺骗、侮辱,让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利益诉求的上访之路。温如风是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他既要面子,也要里子,可孙铁锤又是个飞扬跋扈之徒,你越告,我越欺侮,这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抗,从而加大了基层工作的行政成本与难度。
小说对温如风自然是抱有极大的同情的。他既要追求小康人家的幸福,也要追求做人的尊严和公平正义,这也正是社会演进的总体目标。当然,温如风到后来也有些难缠,且不讲理,长期的上访让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会形塑出一种独特的人物秉性来。温如风之变,自然有他的逻辑自洽。
谈公平正义“英雄在平民中间,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终极目的”
新京报:近年来,我们看到无数像孙铁锤这样的“村霸”及其保护伞被铲除。相对于“大老虎”,群众可能对身边的“小老鼠”更为痛恨。你怎么看孙铁锤这个人物,以及他周围村民的社会欲望?
陈彦:改革开放让无数“捆”在土地上的农民获得了一次身心“解放”。这是一场震撼人心的革命,十分伟大壮阔。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中的北斗村村民,除了留守者继续耕种乡村外,大量年轻人也都奔向了山外能挣钱讨生活的地方。是铁路与高速路建设,让外出的人们又回到乡土,希望找到在“两路建设”沿线挣钱的机会。可这时孙铁锤已经坐大,成为实实在在的“村霸”,利用自己在省城做官的亲戚孙仕廉和各种“人脉”资源,谋得了不少“建设”生意,明显带着极大的盘剥性质,让村民们既要仰仗又暗暗产生了巨大的无奈与痛恨。
村民有村民的目光短浅,以及趋利如水之趋下的本能性情。人都有欲望,围绕着欲望自然也会生发出人性的各种变异、甚至荒唐,北斗村的村民也不例外,他们有时为了仰仗孙铁锤的鼻息,自然也会干出“合谋害人”而不自知的勾当来。
急功近利是一切生命的成长瓶颈,社会发展尤其如此。随着孙铁锤和他的保护伞被铲除,乡村恢复了正常秩序,也逐渐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安北斗的老师草泽明逝世后,他接着重修乡约,就是想从文化精神上重塑北斗村人,而南归雁所推进的生态旅游,则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乡村的面貌。这里面既呈现了过去几十年乡村面临的问题,也叙述了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新京报:小说的最后,善恶分明的派出所所长何首魁现场击毙了“村霸”孙铁锤,自己也牺牲了。这一结尾出乎意料。何首魁最初被温如风视为孙铁锤的保护伞,实则是正义的守护神。如何从何首魁身上理解公平与正义?
陈彦:我始终认为,英雄都在平民中间,素常来自那些不大能看出高人一筹的地方的。如果刻意拔高,不免就有表演成分。何首魁是一个具有巨大人间烟火气的基层派出所所长。由于长年与罪犯或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在他眼中,出了案子,谁都有嫌疑,包括乡镇领导也不能置身事外。
他有他的一套破案经验,也有他的一套面对乡村特殊环境社会治安治理方式。看似不近人情,抑或不讲原则,甚或冷漠无情,脸黑貌丑,但在他内心深处,有大原则、大底线、大关爱。当他充分掌握了孙铁锤犯罪的无数铁证后,在面对人质的安全、以及孙铁锤的狡猾与可能得到“黑伞”庇护的严峻形势下,毅然决然地选择现场击毙恶魔,也将自己的生命和盘托出。
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终极目的。何首魁在所有事情的处置面前,短视看,似乎都有些毛病和短板,但长远看,他甚至堪称公平正义与人间大爱的化身。
谈基层治理“‘信访工作是畅通人民利益诉求的重要通道,正常的上访是来访者的正当权利,不可堵塞”
新京报:小说通过南归雁这个人物,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关系。南归雁担任镇党委书记时力推“点亮工程”,污染了星空、破坏了山林;几年后,他临危受命回去担任县委书记,发现在北斗镇创设“星空”生态旅游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解南归雁的观念变化?
陈彦:整部小说写了一个巨大的认识自然、认识乡村、认识他人、认识自己的过程,每个人都在这场小社会、小宇宙的演进中,重新发现与认识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方位,从而找到一种阶段性定位。村民是这样,干部也是这样,他们是共同的实践者,共同的赢输家,也是共同的觉悟者。
作为这个镇的书记南归雁,在经历了“点亮工程”的失败后,逐渐成为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自然、寻找新的突围的归来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自然应该对他抱有重大期待。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反复试错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南归雁的归来,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我在中国乡村社会完成了儿童、少年、甚至青年的成长期,我对乡村始终心怀敬畏、感恩与感动。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并非我所生长的那个实际乡、实际镇、实际小县城,人物也不能简单对号入座,这就是小说创作的本质。但我可以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的书写中,寄托对乡村更加美好的形塑向往。
今天,我们正呼唤着千万个安北斗、何首魁、南归雁们,脚踏实地去把握规律,带着历史创造性奋力推进乡村振兴。
新京报:写这部小说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你怎么看基层治理的重要性?
陈彦:为写这部小说,我也参阅了大量文件与资料,并进行过一些调查专访。我自己在工作中,也多次遇到类似的事件,并数次参与处置过很是尖锐的矛盾。有的看似简单,但具体到事情上,又确实存在无解的难题。一般都是拖的时间过长,失去了历史真相。有人甚至直接睡在我的办公室逼讨结果。“枫桥经验”始终是我们处理基层矛盾、化解源头风险的宝贵经验。但当温如风遇见了“村霸”孙铁锤时,他不出村去诉求利益,便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孙铁锤又是个上下都有勾结的“村霸”,这就让问题复杂化了。
在我小说所书写的阶段之后,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村霸”之类的“黑恶势力”进行了重拳出击,这正是处理这类复杂问题的综合考量,得力举措。信访工作是畅通人民利益诉求的重要通道,正常的上访是来访者的正当权利,不可堵塞。当然,也有闹访、缠访、无理偏要闹出大理者,这就需要像小说里基层派出所所长何首魁这样的人,不要怕上访,关键是要拿法律依据办事。依法依规面对信访,是处理此类事情的关键。再就是要有温度,要耐得住纷繁琐碎。志在仰望星空的安北斗,就是有情怀、有耐心的基层干部,他十年间几乎就干了这样一件守望“半棵树”的事。他对温如风从不解到呵护的态度变化,也说明做好信访工作的难度和重要性。
谈作家的现实关怀“我以为‘具有悲悯情怀’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奖赏”
新京报:你在后记中说,“一个社会如果缺失了对弱者的悲悯与庇护,将成为同代人要面临的大不幸。”关怀基层、关怀弱者,一直是你的创作主题。为何一直坚持为普通人立传?
陈彦:对弱者的关怀与呐喊,是文学创作的规律性律动。当然我们有各种题材、各种人物值得书写,但作家更有责任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成为文学画廊的平民英雄与主角。从生命的必然死亡看,人与万物无一例外都是值得同情悲悯。生活本身的曲曲折折、悲欢离合,以及由蓬勃健康走向衰老病死的过程,也可归结为熵增定律,其本身就是一场十分悲壮的推石上山运动。
因而,我以为“具有悲悯情怀”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奖赏。悲悯就是深刻认识生活本质、哲学把握生老病死、极大包容天长地短、深入体察致密精微、高怀见物理地去大化善恶美丑,从而书写出带有历史认知长度和现实感通厚度的作品。这个很难,可虽不能至,我们也需心向往之。取法乎上,哪怕仅得其中也是好的。
谈AI对文学的影响“有志于创作的人,哪怕逃到哪个山洞或孤岛上去书写,他独特的写作意义仍将存在”
新京报:你关注新技术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吗?AI是否会取代作家?
陈彦:这已经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几乎在文学的很多场合都在讨论。19世纪西方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就是自然主义,其本质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对待文学创作。一些作家和理论家,甚至提出文学要像解剖学一样严谨缜密,其实是做不到的。
文学就是文学,它天然带着作家独特的想象与创造力,那是渗入骨髓的浪漫、象征、甚至唯美等,不可能成为一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冰凉的解剖刀。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与不可替代性所在。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对文学人物的最深刻理解。从一千个理解者的角度,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哈姆雷特是一道不可能计算完的化学方程式。正是这种丰富性、多样性、化学的持续反应性,带来了文学的不可AI性。
人经过社会不同环境、样貌的形塑后,便会带来“世界上没有一片树叶是相同的”和“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深刻认知。人的创造永远在前,而AI只会进行整合、判断与模仿产出。文学书写是生命个体经验的独特表达,我相信AI能将蒲松龄的494篇小说咀嚼吞噬后,生产出494篇同样神鬼狐怪的小说,但它们应该没有一篇是原创,也没有一篇会有那么神奇诡异的生命独特性,似曾相识将是大概率。
因此,我从来不担心在短期内AI会代替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它只能进行某一艺术类型的创造性复制,可能综合度还较高,但绝不会有阅读的惊艳性出现。即使将来某一天人类失序,被人工智能所控制,生命个体的独特创造仍是不可替代的。有志于创作的人,哪怕逃到哪个山洞或孤岛上去书写,他独特的写作意义仍将存在。
新京报首席记者 何强 受访者供图 校对 刘军